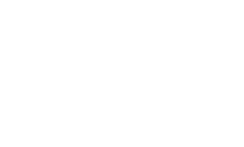摆正“教学中心地位”高校必须彻底去行政化
【深度关度】
编者按
教学是高校的正业和本业,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但它又那么沉重,因为现实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教学压根儿就没在高校占据中心位置,而且越是重点大学,教学就越靠边儿站。本文作者从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重创收轻教学、重外延建设轻内涵发展”等问题中抽离出来,从学术与行政的关系这一视角进行考察和探究,所获得的更为本质和深刻的认知,可能更有利于找到问题的根源与解决的办法。
大学的骨子里为何缺少“为求知而求知”
实事求是地讲,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教学与服务的矛盾,这种现象是共性问题,不独我国有,外国也有;不是今天才出现,历史上就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翻开160年前出版的英国著名学者纽曼所写的《大学的理想》一书,就会知道这一问题在当时是多么引人关注。
学术与行政的关系,说大则大,说小也小。说它大,涉及高等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高校与政府的关系;说它小,涉及高等学校内部学术与行政关系、学校管理者与教师学者关系。不管怎样,在我国,学术与行政关系尤为特别,异常特殊,二者始终缠绕在一起,缠来绕去,到最后总是学术被排挤、被边缘、被淹没,强大的行政力量渗透并支配着高等教育所有领域,大学的一切都被行政化了。这就意味着,在我国高校中,不是教学,不是科研,而是行政管理才真正居于中心位置,大学行政化是教学地位失落的真正原因。
我国有大学行政化的传统,学术与行政从来没有分离过。在古代,学在官府、学术官守,以吏为师。大学一直处于行政管制之下,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成为独立的领地。儒家崇尚学而优则仕,学习和接受教育,第一目的和最高目标是读书做官,骨子里缺少为求知而求知的种子。所谓受尽十年寒窗苦,求取功名天下知;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求知做学问,从来不是读书人的主流价值观。古人也有学问做得很好的,但这些大学问家,往往是在仕途不顺时才改做学问并借以言志的。《左传》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可见,立言做学问实在是他们为官不成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唐诗宋词乃中国文学之顶峰,其间不知涌现出多少文人才俊,李杜诗篇万古传。但要知道,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苏轼……他们都是为官遭贬才成就了文坛至尊地位。
诗在诗外。古人读书从来不为做学问而做学问,从政才是根本目的。在他们心目中,只有从政,才能达成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只有为官,才显示出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如此,那读书和做学问,只不过是从政的敲门砖和为官的跳板。所以,中国没有发展起纯粹的知识,这一点恰好与古希腊古罗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而首先在西方国家出现”,我想答案也许就在这里吧。
“官本位文化”阻碍学术创新和教育进步
大教育家蔡元培的贡献,主要不在于他的教育思想理念多么先进,因为他的教育思想理念其实在德国那里、在欧洲那里几乎就是一种常识。因此,他的贡献其实就在于运用那些先进的大学理念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深刻的改造。众所周知,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就是个名利场,充满着浓厚的读书做官氛围。那时的教师都称呼学生为“老爷”,而蔡元培硬是立志要把大学变成做学问的一方净土。他讲到,读书不是为做官而来,而是为研究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才的学问家。他对北京大学的成功改造,不仅成就了他个人伟业,也使中国大学教育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但这种转型实在太艰难,官本位文化始终高悬于学术之上。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办学和管理高等教育,高校不过是政府的附庸物,其招生、经费、人员编制、领导任命、教授任职、教学计划、教材选用、教学内容等等,无一不是政府安排好的,大学的任务只是执行政府的计划。改革开放后,开始改变政府办教育的管理体制,后来更进一步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是自由、民主、法治和秩序,就高等教育而言,政府必须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强权力的合理配置与制约。
然而,改革的推进并不理想,行政权力至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变相泛化和加深,以至于与现代高等教育制度渐行渐远。正如有人所形容的,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形态上是现代的,在生态上却是传统的;面子是时髦的,里子却是落后的,充斥的是典型的官场逻辑和规则,大学不仅成了政府的下属部门,而且大学内部也等级森严:不同的高校存在着实际的行政级别,从副部长级到正厅级一直到副厅级;从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到分管书记校长再到处长院长系主任一直到行政秘书,一线教师处于行政等级最末端;推而广之,高校课题研究有等级、学术出版物有等级、奖励有等级、项目有级别、人才队伍有等级……一切都被等级化,学术活动行政化。大学教师和学者的活动及其成果,不是来自专家同行的判断与肯定,而是依赖行政等级的认可。行政等级制虽然也有很强的激励作用,但它毕竟是外在的力量,遵循非学术的逻辑,在根本上阻碍着学术的创新和教育的进步。
去除行政化摆正“教学中心地位”
因为官本位文化始终高悬于学术之上,在中国,那些被置于行政等级末端的最广大的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很少体验到学术的自豪感和成就感,而那些居于行政等级上端的少数官员,却掌握和支配着大量的资源,导致所有大学人拼命争抢行政职位,攀爬行政阶梯。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学有所成的教授或博士生导师却宁愿竞聘学校一个办公室副主任或职能部门一个副处长职位的原因。在外人看来,尤其在外国人看来,很是不可思议,但对于高校内部人来讲,教授或博导不过是个学术称号,他们也不过是普通的老师,教授和博导的头衔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切实可支配的资源,但如果他们同时掌握一定的行政权力,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从事学术是一项艰苦孤独寂寞的工作,压力很大,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性或不确定性,教学和研究无法保证人人都能成名成家,成功者毕竟少数,默默无闻者绝大多数。因此,在国人入世精神和当下意识很强的心理作用下,大学知识分子都在权衡着学术与行政的得失,从而会把选择的天平倾向于从政一端,以换取即时的利益和实惠,况且在我国从政从来不会误学问,甚至反过来更能增进“学问”。而政府或高校似乎也愿意顺应人们这种普遍的从政心态,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比如,引进、延聘或者挽留他们认为的某些重要人才,多半会许以一定的官位,同样,某人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也要给予一定的行政职务,如此方能显示对个人的重视。当然,也因此达到对学术、学者管理的目的。官本位背景下,行政及其管理成了大学真正的中心,人们都向往着这个中心,追求着这个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利用着这个中心。无法带来资源、地位、尊严的教学活动沦为学校工作的边缘,一点儿都不显得奇怪。
落实教学中心地位,如果不改变大学官本位的体制和机制,不确立学术至上的观念与制度,是根本行不通的。好在国家已经注意到学术行政化的弊端和危害,明确提出要去除高校的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教育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去行政化也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也罢,目的都在于改变政府与高校间的关系,正本清源,学术与行政各归其位,各司其职,该是上帝的还给上帝,该是恺撒的还给恺撒。同时还要构建现代化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真正还学术以尊严、还学者以尊重、还知识以尊崇。什么时候我们确立了学校本位、学术本位、学者本位,我们的大学就必然会走向兴旺发达,学术创新和活力就会如泉喷涌,教学的中心地位就会得以真正落实,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作者刘振天 系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研究员、博士)
2014-04-01 06:56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